2月27日,法国《电影手册》编辑部宣布全体辞职,引发热议。这本传奇电影杂志引领了半个多世纪的影像先锋,此次编辑部集体辞职意味着“手册精神”的再次不朽。在辞职声明中,编辑部讲述辞职缘起:杂志易手东家后,股东成员增加八名制片人,编辑部担心“高度介入、表明立场的批判性杂志”会受到明显的利益冲突,无法保持独立性,因此集体辞职。
6月15日,著名学者、电影文化研究专家、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做客北大博雅讲坛,谈到这一事件,她在感到震惊之余,再次想起 “电影已死”的陈旧话题。自柯达公司申请破产、最后一间洗印厂关闭起,似乎每次技术革新时都有人叫嚣“电影已死”。不过,这些对戴锦华的冲击都没有《电影手册》编辑部集体辞职来得深刻。“对我来说,《电影手册》从来不是什么拥有亿万读者的大型商业杂志,它一向标示着极端小众、个性化的先锋性。此次《电影手册》编辑部集体辞职,如果没有后续“复活”的迹象,电影可能真的死亡了。”
独一无二的“手册精神”
《电影手册》由法国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创建于1951年4月。当时,团结在巴赞身边的是一批迷影青年兼影评人,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戈达尔、特吕弗、夏布洛尔、侯麦和里维特。这五位是《电影手册》编辑部的第一代成员,后来成为法国 “新浪潮”的中坚力量。他们从写影评开始,转身执导电影,对世界电影的美学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
安德烈·巴赞
《电影手册》以独立敢言著称,有独特的美学判断和价值诉求。对于受到艺术电影最高殿堂——戛纳电影节褒奖的金棕榈电影,《电影手册》也敢公然“开涮”。譬如2015年和2016年的金棕榈获奖电影《流浪的迪潘》和《我是布莱克》就曾受到《电影手册》编辑部的严厉批评。编辑们普遍认为这两部电影都主题先行,缺乏原创性,形式上看非常传统,表达也很陈旧。这样的电影向观众传递常见的社会问题,观点先行,而一味忽视电影美学,反而影响电影在表达社会问题时本应有的感染力和深度。

“新浪潮”双子星:戈达尔(左)和特吕弗(右)
《电影手册》既是艺术的,也是政治的,编辑们在写评论的时候不仅考察电影的美学表达,同样关注电影的生产机制。戴锦华认为,《电影手册》的重要性正是体现在这里。“《电影手册》有着双重参数:一是对电影美学的不断倡导和推进,对好莱坞资产阶级美学的颠覆,挑衅古板的电影叙述模式;二是其激进的政治性,《电影手册》编辑们认为电影要介入现实,对现实有所承担。“”《电影手册》另一重大贡献是向欧洲积极引介非西方国家的电影,同时关注法国电影的美学由来。”

《流浪的迪潘》剧照
戴锦华理解《电影手册》编辑们批判两部金棕榈电影的出发点,但她对《流浪的迪潘》和《我是布莱克》表现出的社会诉求仍然表示认可。《流浪的迪潘》首映6个月后,巴黎发生“11·13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电影对现实有了某种前瞻性预见,这让戴锦华对选择《流浪的迪潘》为金棕榈奖的评委会肃然起敬,“说明评委们对欧洲的民族矛盾和种族问题有一定的敏感度。”

肯·洛奇
《我是布莱克》的导演是英国国宝级导演肯·洛奇,从影超过半个世纪,两次获得金棕榈大奖。肯·洛奇的电影关注底层人民的生活,讲述平凡人的故事,以此生动展现英国劳动人民的艰辛和傲骨。戴锦华表示自己一直持续关注着肯·洛奇的电影创作,并有某种偏爱。“肯·洛奇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他的坚持,他将目光投注在形形色色的小人物身上,不是出于一种廉价的人道主义,而是极端朴素的阶级情感。肯洛奇的电影让你感觉到他真正站在底层人民中间,这不是一种外来的、带有距离感的视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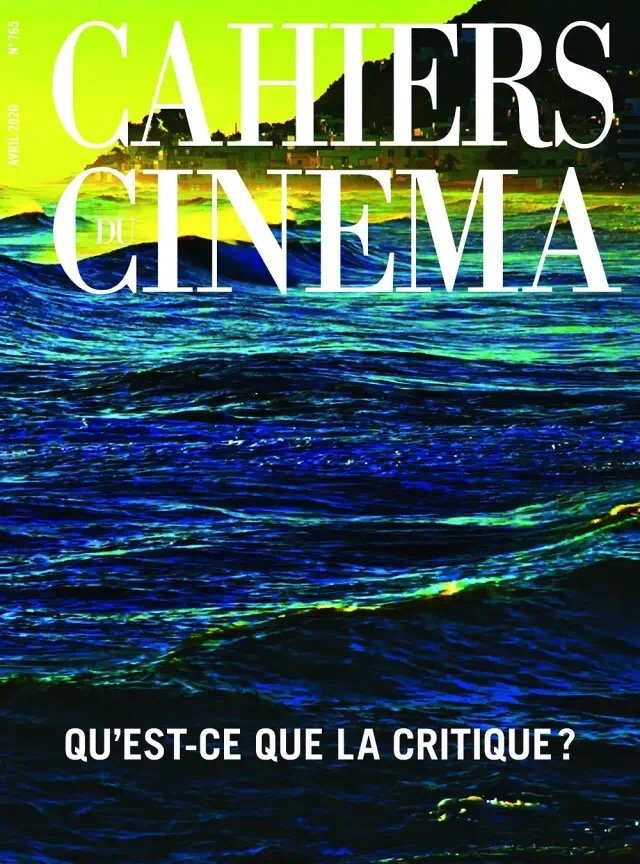
《电影手册》765期,2020年4月
《电影手册》编辑部集体辞职后,在今年4月推出最后一期。在这期卷首语中,编辑们写道:“电影之力需由爱来解开,是连续的爱的扣环让我们喜欢一部电影:充斥其中的情感,对于每个细节和整体辩证的用心,为了作品而不遗余力完成的爱意 (库布里克)。热爱我们所做,同谁做,以及为何而做的——爱的艺术。”戴锦华认为只要有这种爱,“手册精神”不朽,电影不死。
戛纳、奥斯卡和《寄生虫》
《悲惨世界》剧照
戴锦华将各大电影节当做了解世界电影发展的线索。她认为,当今世界有如此众多的国际电影节,每年入围影片基本上可以涵盖当年重要的电影。在疫情宅家期间,她正好“恶补”了去年入围各大电影节的重要电影,其中一部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的法国电影让她喜出望外。这部电影叫《悲惨世界》,与法国文豪雨果代表作《悲惨世界》同名,讲述以巴黎39区为背景的街区暴力事件。巴黎39区据说曾是雨果写作《悲惨世界》的地方,现在聚居着大量来自阿拉伯世界和北非的新移民。《悲惨世界》通过马戏团一只狮子的丢失事件为引线,展现街区暴力和黑帮争斗,最后导向对孩童暴力的探讨。“‘悲惨世界’并没有过去,很多巴黎人只关注自己的生活,不知道39区发生了什么?这是一座被折叠的巴黎。”“《悲惨世界》的导演没有做表态,这值得赞赏。而且电影的戏剧性很强,同时置入众多社会议题,有很强的话题性。”

《寄生虫》海报
去年同样兼具艺术性和商业性的重要电影还有韩国电影《寄生虫》,这是一部让戴锦华觉得“不可思议”的电影,因为它同时获得了戛纳金棕榈奖和奥斯卡最佳影片。“对金棕榈而言,《寄生虫》太商业化了,对奥斯卡来说,《寄生虫》又太激进,两个奖项看起来都不太适应,最后竟然共享了。最有趣的或许还是奥斯卡,《寄生虫》作为一部韩国电影获得最佳外语片(现已改名为最佳国际电影)毫不奇怪,但同时包揽最佳原创剧本、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实在可以说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寄生虫》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确实让人意外。作为“美国电影的家宴”(作家阿城语),奥斯卡主要表彰美国本土电影,现在却将最高奖颁给一部讲韩语的韩国电影。
奉俊昊
《寄生虫》导演奉俊昊是土生土长的韩国人,在两部具有极高艺术性的类型电影《杀人回忆》和《汉江怪物》之后,迅速成长为国际知名导演,顺理成章地执导了《雪国列车》和《玉子》这两部由大型国际资本运作的商业片。奉俊昊的电影完美平衡了艺术性和商业性,镜头语言也是十足好莱坞式,这是《寄生虫》获得奥斯卡青睐的重要原因。戴锦华认为,《寄生虫》除了价值观特别苦涩外,没有其他不适合拿奥斯卡最佳影片的。“《寄生虫》非常观念化,讲述在一种阶级固化的社会环境中,底层人民向上攀爬结果彻底坠落的故事。它有韩国式的犀利批判,与奥斯卡的基调不太吻合。”
戴锦华介绍说,“奥斯卡一直表彰表现美国主流价值观的好莱坞电影,代表着好莱坞电影工业迄今为止建立的最快反应机制,好莱坞的商业性建立在对现实的极端敏感上,建立在某一种对现实的高度紧密的认知上。奥斯卡把奖给《寄生虫》再次表明好莱坞的敏感和绝望,好莱坞已经走到无法在自己生产的电影中选择一部代表作的困境。好莱坞作为世界电影工业的重镇,在当下受到的冲击和围困是多方面的:胶片死亡、数码转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介入、人才资源流出、影院关门等等。”
在对好莱坞造成冲击的众多元素中,流媒体“网飞”(Netflix)扮演了重要角色。流媒体的兴起,正在加速影院的消亡。戴锦华将“网飞”比作《浮士德》中的梅菲斯特,扮演“给电影投资,买电影灵魂”的角色。好莱坞对此并非没有回应,大量生产漫威电影便是重新赢取观众的一种对策,虽然这一做法受到不少好莱坞一线影人的反对。
“奥斯卡将最佳影片颁给《寄生虫》,如同好莱坞给自己下的一剂猛药,以此换回它内在的动力。大家对好莱坞有一种成见,认为好莱坞以中等预算规模的类型片为支柱,与全球中产阶级直接互动对话,但现在好莱坞在全面衰退和丧失,这是电影危机的表现。同时应该看到,好莱坞衰败的过程中,艺术电影也在全面危机当中。”
保卫影院,保卫电影
电影的危机,自上个世纪有声片诞生开始,便不断回响在历史的叙事中。尤其是电影死亡的话题,重新引导人们反思电影到底是什么?早在上世纪50年代,安德烈·巴赞出版了他关于电影研究的论著《电影是什么?》,书中收录巴赞在《电影手册》和其他报刊杂志上发表的大量追问电影本体的文章。巴赞为二战后兴起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艺术特色、美学价值做了全面总结,并影响法国“新浪潮”运动的诞生。作为电影理论研究的地标式著作,《电影是什么?》在业界享有崇高的声誉,被誉为“电影的’圣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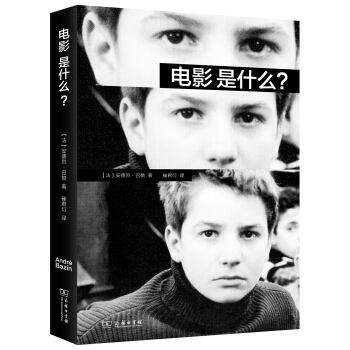
《电影是什么?》中文版书影
戴锦华认为“电影是什么?”在数码时代必须被重新回答。原因在于,巴赞展开电影本体论的研究建立在胶片物质性的基础上,而当代绝大数电影以数码的形式呈现,因此,必须重新回到“电影是什么?”的问题。“胶片电影衰落后,电影开始无穷蔓延。数码技术带来的是电影制作门槛的极度降低,看起来似乎每个人都能简单地制作电影。”戴锦华不认为这是一种好现象。
电影的英文表达有三个词汇,分别是movie、film、cinema。其中movie指故事片,film指胶片,cinema指影像,同时cinema也与影院紧密相关。戴锦华认为,电影作为20世纪一门伟大的艺术,影院是它基本的生存空间。胶片消亡后,电影的放映形式发生了改变,但影院作为电影的媒介形态并未变化。戴锦华联想到今年年初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影院关门歇业,去影院观影成为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这让她感到特别的悲哀。她笑称“新冠疫情让每个人都体验到了一种希区柯克式的现实。”
她坚持电影作为一门影院艺术的独特价值。“影院是20世纪留给我们仅剩的社会空间之一。数码技术造成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体验不到社会性。隔离之后,我们对社会性的依赖是前所未有的,只有当社会有序运作,我们才能顺利地’宅’。影院作为最后的社会空间,是一个让我们重新体验社会性的场所,这是电影作为一门艺术的非电影诉求。”
“电影是一门及物的艺术”,巴赞说过千万次,只有当我们拍摄他者而忘却自我时才有意义。“透过镜头是望向他人,还是自我凝视?”戴锦华坚定表示,电影必须重新找到与现实的对话,这样电影才能不消亡。 (中国作家网记者 刘鹏波)
(图片来自网络)
(更多好文 请加小编微信happy_happy_maom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