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悦然
瑞典著名汉学家马悦然先生(Göran Malmqvist)于2019年10月17日卒然仙逝,而就在那之前一年半左右时间,即2018年3月,我才和他见过面。那时我和家人去斯德哥尔摩参加瑞典皇家人文学院庆典,发邮件希望和他见面,悦然先生和夫人陈文芬女士邀请我们在斯德哥尔摩著名的大旅馆(Grand Hotel)午餐。我们到约定地点不久,便见他们夫妇一起过来。那时悦然先生已是九十四岁高龄,鹤发银髯,策杖而行,面容清臞,闲淡自若,宛然有仙风道骨之态。他告诉我们说,近一年多来,因为脊椎有些病变,引起背部疼痛,不得不减少活动。但他又豁达自解,说上天已十分眷顾,他活了九十多岁,身体状况一直很好,这一点病痛实在不应该抱怨。我们接谈甚欢,临别时还意犹未尽,相约不久再聚。2019年10月18日,悦然的学生、接替他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任汉学教授的老朋友罗多弼(Torbjörn Lodén)发来电邮,告诉我悦然已在前一天辞世。得此噩耗,一年多前在瑞典见面时悦然的音容笑貌,犹历历如在目前,想来那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使我不禁黯然神伤,心中一阵悲戚。
我第一次与悦然先生见面,应是在1996年5月间,那时罗多弼邀请我作为校外主考,从美国加州到斯德哥尔摩大学,去参加一位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博士生的论文答辩。在瑞典的几天时间,使我对这个具有独特风情的北欧国家初具印象,而感受尤深者,就是瑞典的汉学传统。这个北欧国家离中国有万里之遥,却居然有不少学者和学生认真研习中国从古至今的历史、语言、文学和文化,令我深为感动。十七世纪末,已有两位瑞典学者用拉丁文撰文,讨论中华帝国和中国长城,这说明当时在欧洲,尤其在法国十分流行的所谓“中国风”(chinoiserie),在瑞典也有相当影响。二十世纪初,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于1901年在新疆罗布泊以西的洪荒大漠之中,发现了已经消失千年之久的楼兰古城;另一位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 1874-1960)在1920年代参与中国考古,在周口店发现了北京人,又在河南发现了仰韶文化。不过赫定和安特生都不懂中文,所以瑞典作为学术研究的汉学传统,应该说开始于由研究古汉语音韵学而著名的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8)。马悦然就是高本汉的学生,而他又是罗多弼的老师。我到瑞典之前,早已听说过马悦然,知道他是瑞典皇家人文学院院士,而且是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学院中,唯一懂中文的院士。我也知道他像他的老师高本汉一样,研究中国的方言,尤其是四川方言。我和东方语言文学系的教授和研究生见面聚会时,悦然也来参加。他显然知道我是四川人,一见面就和我讲很地道的成都话。1948至1949年间,他在四川考察方言,曾在峨眉山报国寺住过,又在成都进一步做研究,租用了化学家陈行可教授家的一个房间,也因此和陈教授的女儿陈宁祖相爱,后来结为夫妇。在悦然的生活和学术生涯中,成都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1996年我去瑞典时,陈宁祖正在重病之中,之后不久就去世了。我想,那时悦然见到一个在成都出生长大的人,大概有他自己一番特别的感慨吧。那是我们初次见面,在远离四川的异国他乡听到悦然讲成都话,使我也感到格外亲切。

马悦然与陈宁祖
我后来到瑞典和悦然见过多次,也曾请他到香港城市大学访问讲学。2009年2月,我获选为瑞典皇家人文学院外籍院士,并应邀10月间到皇家学院演讲。悦然告诉我说,在我之前,诗人和批评家冯至先生是获选为瑞典皇家人文学院外籍院士的第一位华人学者。早在1956年至1958年,悦然在瑞典驻北京使馆工作时,就与老舍、何其芳、艾青等中国作家和诗人时常来往。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悦然又有机会到北京,与沈从文、钱锺书、王辛笛等文坛和学界的许多知名人士见面,更与时任社科院外文所所长的冯至先生成为好友。后来冯至先生获选为皇家人文学院外籍院士,应邀到斯德哥尔摩去做关于德国诗人里尔克的演讲。2009年我在皇家人文学院的演讲则是从中西比较的角度,讨论人与自然之关系。我讲到中国天人合一的观念,但不是像有些人那样,把天人合一说成是人与自然交朋友,代表了东方人重视和谐的综合性思维,而西方人则是分析性思维,是征服自然,破坏自然,造成环境污染等全球性的各种问题,而中国人的天人合一则可以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一种治理的良方。我认为这种把中西绝然对立起来的文化相对主义,既不符合中西文化和思想传统的实际,更不利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
要讲天人合一,很重要的文本依据应该是汉儒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董仲舒应汉武帝之召对策,使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而他以天人感应为基础,在《春秋繁露》里为皇权统治的合理性,提供了一套宇宙论和政治论的论述。董仲舒说人身上有四肢,有五脏,有十二个大关节,有三百六十六个小关节,正符合一年的四季、阴阳五行、一年的月数和日数。甚至眼睛的张合,鼻口的呼吸,也符合昼夜交替和风气之流动,所谓“身犹天也”。儒家以人为本,人和自然绝非平等。董仲舒说其他动物都“莫不伏从旁折天地而行,人独题直立端尚,正正当之”,由此可见“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所以中国的天人合一根本不是人和自然交朋友,而是人高于天下万物,最近于天。于是观天象可以测人事,并由此作出君权神授的解释,使皇权有了神圣的合理性。但以天或自然与人的身体器官相副,却并非中国人独有的思想。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希腊等不同的古文明里,都有观天象以测人事的类似观念,在中世纪到早期现代的欧洲,也有自然之大宇宙(macrocosm)与人之小宇宙(microcosm)互相对应的观念,还有所谓身体政治(body politic)的观念,把人的身体器官与国家的组织机构相比附。所以人与自然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都呈现出复杂的关系,而且往往是人化的自然。
悦然对我的演讲特别感兴趣,因为他曾经研究并翻译了《春秋繁露》,但译稿尚未发表,我的演讲重新引起了他对《春秋繁露》的兴趣。他告诉我说,有些学者对《春秋繁露》究竟何时成书、是否为董仲舒所作,都提出过质疑,但我们同意,无论这当中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董仲舒和《春秋繁露》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意义和影响,都毋庸置疑。与悦然谈论中国的经典,谈起他多年研究和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经验,我可以感觉到他对中国、对中国文学和文化传统怀有深厚的感情。
悦然曾在1980年代两度担任欧洲汉学学会主席,与人类学家、台湾蒋经国基金会执行长李亦园交情甚厚,成为基金会欧洲委员会主席。他和捷克布拉格查尔斯大学研究鲁迅和现代中国文学的普实克教授(Jaroslav Prušek, 1906-1980)是好友,两人又同为高本汉的学生,所以他和捷克研究中国的学者们都很熟悉,便协助蒋经国基金会在查尔斯大学建立起在欧洲的联络中心。悦然对台湾文学也颇为关注,曾翻译了包括郑愁予、纪弦、罗青、商禽等台湾诗人和作家的作品,后来还翻译了诗人杨牧的全部作品。悦然在晚年认识了来自台湾的陈文芬女士,并于2006年正式结婚。在陈文芬协助之下,他更进入用中文来翻译和创作的新领域,用中文翻译了瑞典诗人、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特朗斯特罗默(Tomas Tranströmer, 1931-2015)的诗集,并在2002年之后,陆续发表了散文集《另一种乡愁》、诗集《俳句一百首》和一本微型小说《我的金鱼会唱莫札特》。

《另一种乡愁》

《俳句一百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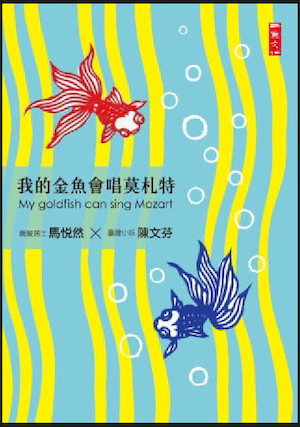
《我的金鱼会唱莫札特》
作为汉学家,悦然翻译过不少中国古代经典,包括《道德经》《水浒传》《西游记》《辛弃疾词》和其他古典诗词,但翻译得更多的是当代的文学作品。由于诺贝尔文学奖只颁发给活着的作家,而评奖的瑞典学院十八位院士们大多只懂得主要的欧洲语言,所以对中文和其他非西方语言的文学作品而言,优秀的翻译对这些作品能否获奖就尤其重要。悦然曾翻译老舍、沈从文、北岛和八十年代朦胧诗人的作品以及莫言、李锐、张贤亮、曹乃谦等作家的小说。他深感遗憾的一件事,就是1988年沈从文很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在最后决定之前,沈先生却病故辞世了。悦然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极力使中国文学能够得到西方更多读者的欣赏和赞许,并争取中国作家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可以说这是他一生事业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不过文学作品的评价向来是诗无达诂,见仁见智,很难达到完全一致的意见,所以诺贝尔文学奖自1901年开始颁发以来,就一直争议不断。虽然有些重要的作家和诗人获奖,如泰戈尔、叶芝、萧伯纳、托马斯·曼、T. S.艾略特、海明威、加缪、马尔克斯、奈保尔等等,但也有更多批评家们公认为重要的经典作家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如托马斯·哈代、普鲁斯特、亨利·詹姆斯等等。由于诺贝尔文学奖往往引起争议,悦然又是瑞典学院的院士之一,这固然使他在华人社会里名声很响亮,但与此同时,也难免使他陷入相关的争议,受到不少人质疑甚至攻击。
大概也就在2012年左右,网上盛传钱锺书曾有直斥马悦然的一段话,而且说得相当难听。据说那段话最初的来源,是发表在1995年《传记文学》里的一篇文章,说马悦然去拜访钱锺书,钱先生竟当面斥责他“仗着我们中国混你这饭碗”,又说:“在瑞典你是中国文学专家,到中国来你说你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的专家,作为汉学家,你都做了些什么工作?”还说:“别的国家都可以用原文参加评奖,中国作品就非得译成英文才能参评,有这道理吗?”这种传言众口铄金,伤害力极大。且不说有人登门拜访,却当面骂客,把话说得那么难听,这不符合中国人待客之道,让人很难相信钱先生会这么做。钱锺书文采斐然,就是讥刺人,也会把话说得与众不同,绝不会像这几句话那么直白无趣。马悦然作为汉学家做的许多工作,钱先生不可能不知道,诺贝尔文学奖需要通过主要西方语言的翻译,才可能使瑞典学院的院士们得以去评审,这些都是常识,钱先生更不可能不知道。但更可疑的是,如果这真是马悦然登门拜访时,钱先生当面对马悦然说的话,《传记文学》那篇文章的作者并不在场,钱先生也向来不同意现场录音录像,那么对这段传言,谁又可以当场记录,并写成文字呢?这不能不让人想起钱锺书先生自己在《宋诗选注》序里的一段话。《左传》有一段值得怀疑的记载,钱先生评论说:“《左传》宣公二年记载鉏麑自杀以前的独白,古来好些读者都觉得离奇难以相信,至少嫌作史的人交代得不清楚,因为既然是独白,‘又谁闻而谁述之耶?’”我们可以借用钱先生自己那句话,来问一问那篇文章的作者,如果当时钱先生说了这段话,那又是“谁闻而谁述之耶”?
2013年3月22日,悦然传给我一篇短文,对此事做了说明。他在邮件中说,他自己并不在乎那些传言,但这些流言蜚语涉及一位已故去的朋友,则使他很恼怒。他用英文写的声明说,“我和钱锺书先生及其夫人杨绛见过两次。我们第一次见面在1981年夏天,第二次见面在1982年8月”。悦然说这两次见面,都是和钱先生讨论欧洲科学基金会资助而由他负责的一个研究项目,内容是关于1900年至1949年的现代中国文学。这个项目完成之后,在1988年至1990年之间,由莱顿的布里尔出版社分为四卷出版,分别讨论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和戏剧。悦然说,1982年第二次与钱先生见面时,钱先生告诉他说,许多中国作家和诗人能够入选他负责的那个项目,在西方没有被忘记,都对悦然表示感谢。钱先生还写信给在上海的王元化先生,介绍悦然到上海去拜访王先生。悦然的声明还说:“我在1985年成为瑞典学院的院士。在与钱锺书先生见面时,我们从未讨论过涉及瑞典学院的事,也没有讨论过我翻译中国文学的工作。我对钱锺书先生及其夫人杨绛一直怀着最高的敬意。他们给我的印象,也是他们珍视我在西方为扩大对中国文学的认识和鉴赏所做的努力。”1981和1982年,我正好在北京,时常和钱锺书先生见面交谈,并经常有书信来往。在我和钱先生的很多次交谈和更多的通信当中,我从来没有听钱先生提到过类似这种传言的话,我也不相信这种毫无根据的流言蜚语。
我与悦然2018年3月最后那次见面,他说起他正开始翻译《庄子》,译第一篇《逍遥游》若有神助,很快就完成了,可是从《齐物论》以下,就颇费思索,不能不字斟句酌,仔细推敲。罗多弼曾告诉我说,悦然的文笔很优美,所以他的翻译也特别受读者欢迎。可惜我不懂瑞典文,只能想象悦然以优美灵活的译笔,把庄子那汪洋恣肆、妙喻无穷的文字重新转达出来,会是如何美妙的文章。我回到香港后,曾和悦然通过电邮,他告诉我说,翻译《庄子》是他“自1950年代初就有的一个梦想”。在中国先秦典籍中,《庄子》是一部奇书,《天下》篇所谓“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这几句话,可以借用来描述《庄子》这部书本身的语言特点。我不知道悦然后来翻译了多少,但到近百岁的高龄来圆年轻时候就开始的梦,而且与思想如此深邃、想象如此丰沛,语言又如此奇瑰的一部经典结伴同行,走完人生最后的一段旅程,对把一生精力都奉献给中国文化的一位学者而言,那或许是最好,也最合适的选择和归宿吧。
(更多好文 请加小编微信happy_happy_maom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