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名单即将于明天揭晓。这几天,中国女作家残雪突然成为网络热词,这都归因于一家博彩公司的榜单。在英国博彩公司NicerOdds公布的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赔率榜上,中国作家残雪、余华、杨炼等榜上有名,其中排名最高的是残雪,一度排在第四位。
尽管残雪在国内普通读者中的知名度并不高,但她的作品在国外具有相当影响力,今年三月获得国际布克奖提名就是一个例证。此外还有一些流传已久的著名传说,比如说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曾称残雪为“中国的卡夫卡”,另外还有一个说法是说苏珊·桑塔格也十分推崇残雪,更有不少标题称她为“最接近鲁迅的作家”。
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北大中文系教授戴锦华在其文章《残雪:梦魇萦绕的小屋》中对其作品的评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残雪是当代中国文学中,唯一一个几乎无保留地被欧美世界所至诚接受的中国作家。笔者毫不怀疑有诸多中国作家比残雪拥有更高的国际知名度,但残雪或许是唯一一个似乎不必参照着中国、亦不必以阅读中国为目的而获得西方世界的接受与理解的中国作家。”

残雪:梦魇萦绕的小屋
文 | 戴锦华
本文原载于《南方文坛》2000年第5期,本次发表有删节

戴锦华,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教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文学系11年,自1993年任教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现为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从事电影、大众传媒与性别研究。开设“影片精读”“中国电影文化史”“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性别与书写”等数十门课程。中文专著《雾中风景》《电影批评》《隐形书写》《昨日之岛》《性别中国》等;英文专著Cinema and Desire, After Post-Cold War。专著与论文被译为韩文、日文、德文、法文等十余种文字出版。
独步之作
在80年代,乃至当代中国文学史的版图上,残雪堪称独步。不仅是作为文化的个案,而且是作为文学的特例。残雪独步于当代中国的文学惯例与80年代的文化时尚之外,独步于中国当代文学“无法告别的19世纪”之外。她展示了一个怪诞而奇诡的世界,一处阴冷诡异的废墟,犹如一个被毒咒、被蛊符所诅咒的空间,突兀、魅人而狰狞可怖。

作家残雪,原名邓小华。祖籍湖南耒阳,1953年5月30日生于长沙。先锋派文学的代表人物。残雪从小敏感、瘦弱、神经气质,短跑成绩和倔强执拗在学校都很有名。她小学毕业后恰逢文化大革命爆发,便失学在家。1970年进一家街道工厂工作,做过铣工、装配工、车工,当过赤脚医生、工人,开过裁缝店。1978年结婚,丈夫是回城知青,在乡下自学成木匠。1980年残雪退出街道工厂,与丈夫一起开起了裁缝店。残雪自小喜欢文学,追求精神自由。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2015年,残雪的作品获得美国纽斯达克文学奖提名;获得美国最佳翻译图书奖提名;获得英国伦敦独立外国小说奖提名。2019年她凭借长篇小说《新世纪爱情故事》入围国际布克奖长名单
围绕着残雪和她的作品,是一份鼎沸般的众声喧哗和更为持久的寂然冷漠。尽管整个80年代,中国文坛充满了对“现代派”、“先锋文学”的呼唤与饥渴,残雪的小说因此在引起了短暂的骚动之后,获得了“宽容”的接受乃至拥抱,但面对残雪,人们的拥抱——因其印证了进步之旅,满足了我们对现代主义的中国文学的渴望——多少显得迟疑、暧昧。因为残雪的文学世界在我们所熟悉的文学惯例与批评惯例中显得如此的怪诞、陌生,甚至全然不可解,因此她令人无语。
90年代以来,除了少数残雪作品始终如一的拥戴者和女性评论家之外,残雪的作品已较少为人所提及。这份缄默与谨慎,不是或不仅是面对奇迹的震惊、折服与无语,而或多或少带有几分无力、无奈和恼怒。
残雪的小说世界似乎在不断提示着某种进入其文字迷宫的路径,她作品中的某段文字,人物的某种姿态或行为似乎在提示着某种我们似乎极为稔熟的生活;最为经常而直接的,残雪小说所呈现的世界,令人联想起拒绝和批判视野中“中国的岁月”,尤其是“文革”时代的梦魇年代。那是一处被窥视、被窃窃私语、讪笑所充塞的空荡的空间,一片被污物、被垃圾、被腐坏的过程所充塞着的荒芜,一个被死亡、被恶毒和敌意所追逐着的世界;那永远喋喋不休的抱怨和“对话”——发出的语词永远如同触到了玻璃的利物,除却制造尖锐刺耳的噪音,永远不会抵达对方;彼此充满了刻骨仇恨的人们却时时刻刻地厮守并面面相觑。

但是继而人们便会发现,被那些昭然若揭的路径所指引,甚至在这似乎被精巧的玄机所结构的迷宫入口处,我们已然碰上了死路或绝壁。她笔下的“黄泥街”或“五香街”似乎无疑是某类、某处现实的镜中像或微缩本;但作为读者或阐释者,我们不仅无法复原其原型,相反很快便迷失在残雪以意象、幻象,醒来时刻的梦魇,或死亡之后的苟活所集合起的文字魔幻中。
如果说,深刻影响当代中国文学的那一“无法告别的19世纪”,留给我们的是对完整的情节链条:被叙事件的内在逻辑、因果链条的完整,空间在连续的、线性的时间线索中变换推移,有性格、至少是有特征、有理据的人物,意义与终极关怀(诸如真善美)的需求,那么我们在残雪的世界中,不无惶恐地发现这一切均告阙如。
1985年,当残雪的作品以喷发般的方式,涌入了中国读者的视野,几乎像是在制造某种灼伤。她的作品中充满了被突兀诡异的意象连缀起来的跳跃的句子,而那意象充满丑陋的、几乎可以感觉到那腐坏/死亡过程的身体,在酷热或潮湿阴冷中滋生的爬虫,如同苔藓一般无所不在地附着的敌意和诅咒,恶毒的梦呓和迫害妄想式的谵妄,在雨水和潮湿中流淌的垃圾、恶臭和流言、私语。所谓:
一个噩梦在暗淡的星光下转悠,黑的,虚空的大氅。
空中传来嚼骨头的响声。
猫头鹰蓦地一叫,惊心动魄。
焚尸炉里的烟灰像雨一样落下来。
死鼠和死蝙蝠正在地面上腐烂。
苍白的、影子似的小圆又将升起——在烂雨伞般的小屋顶的上空。
如果说,80年代中期波特莱尔及其“恶之花”的复现,使“审丑”说的盛行,以别一方式渴求着现代主义文化在临中国,但面对残雪,人们却无疑难于承受其中那盈溢着邪恶而争相绽放的意象之花;《你别无选择》中的混乱与无行,似乎已到达人们所能承受的上限。因此,残雪的支持者便以鲁迅所谓“真的恶声”来为之申辩。或许同样令人们难于直面的,是在这片邪恶的风景中,残雪确乎使其渗透着一份从容的诗意:
我穿透玻璃世界的白光,匆匆地向前走去。
“你,想伪装么?”灰衣人在林子劲头截住我。那人没有头,声音在胸腔里嗡嗡作响。
我听见背后叮当作响,那个世界正在破碎。
“不,不,我只想换一套内衣,换一双鞋,然后把头发梳理整齐,很简单的事情。如果有可能,我还要制作蝴蝶的标本,那种红蝴蝶。在冬夜里,我将细细地倾听那些脚步声,把梧桐树的故事想个明白。外面很黑,屋里也很黑,我用冰冷的指头摸索到火柴,点出一朵颤抖的火苗。许多人从窗前飘然而去,许多人。我一伸手就能触到他们的肉体,我咬噬他们的脸颊,私下里觉得很快意。我要在暗夜里坐到最后一刻,冷冷地微笑,温情地微笑,辛酸地微笑。那时油灯熄灭,钟声长鸣。”我终于对自己的声音着了迷,那是一种柔和优美的低音,永恒不息地在我耳边倾诉。
那无疑是一份诗意,地狱间的诗情,只是它并不朝向天堂。诚如夏洛特·英尼斯所言:她是“出自中国的最为现代的作家”。“残雪在中国文学中是一个异常。……毫无疑问,就中国文学水平来看,残雪是一种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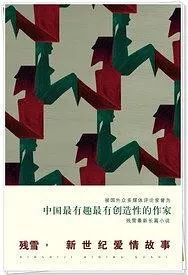
不错,如果就震动、断裂与异样的陌生感而言,残雪确实是一场革命,但这场“革命”并未产生某种必然与革命相伴随的结果:中国文学的主流书写方式并未因此而有所改变,甚或没有足够响亮的回声。
尽管残雪的出现与存在,的确多少改写了人们关于“文学”或“中国文学”的想象,拓宽了中国文学的疆域。但事实上,尽管在残雪之后,“先锋文学”一度成了中国文学的主潮,但在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脉络中,残雪仍是不可重复、不可复制——她的异军突起,让人们一度忆起在20世纪已渐被遗忘的关于天才与奇迹的神话;而1985年的残雪确乎如同一个神话,一个于未知处降落的不明飞行物,携带着梦魇、语言所构造的恐怖与绝望的地狱而盈盈飞动。
残雪·中国与“世界文学”
似乎没有人怀疑中国的土地和岁月造就了残雪,没有人怀疑残雪与丰饶、陌生而事实上在中华正统文明中被逐至边角的楚文化的、或许是不无幽冥的连接;但人们却无从在中国的文学脉络间为残雪找到其出身和出处。于是,人们不得不赞叹在另一种情况下常显得语焉不详的“想象力”。
毋庸置疑,残雪的作品充满了飞扬灵动的艺术想象力;尽管同样没有疑问,那想象力所建构的世界经常令人毛骨悚然,或濒于作呕。一如残雪小说的一位美国评介者所言:“没有任何读者能够从她那强有力的幻想梦境中挣脱出来而不受伤害,她的作品既是美丽的又是危险的。”

作为残雪创作生命喷发的年代,她从那条肮脏、腐烂、绝望而躁动的“黄泥街”上向我们走来,仿佛掀开一本子虚乌有的日历(或历史?),在每一页被肮脏的污物变得黏腻的纸页上渐次显现出梦魇般的画面;如果你被某种稔熟的因素所吸引,试图去辨识这图画,那么你或许会被噩梦重现的惊悸与不可抑制的厌恶攫住。
但间或不能自已,你会瞩目于残雪作品中若隐若现的智性的游戏,一种发现其游戏规则的好奇与乐趣会使你再度冒进。或许残雪小说最为有力的评述者之一近藤直子的话是进入残雪世界的标识之一:“残雪的故事不是世界内部的故事,而是关于世界本身的故事,不是时间内部的故事,而是关于时间本身的故事……”当残雪伴随她的X女士“脚步轻快,在五香街的宽阔大道上走向明天”的时候,梦魇的重重魅影在骤然的涌现之后,似乎多少变得轻薄、透明;残雪作品已更为清晰地显现出其机敏、智慧的文学/叙事游戏的特征。

至少在笔者眼中,残雪作品并非“中国故事”或“民族寓言”;尽管她的笔法与基调间或令人想起先师鲁迅。但残雪那被梦魇萦绕的小屋,那被苍老的浮云所重压着的村镇,并非鲁迅的“铁屋子”的幻化;而残雪作品中那份极为平静以致无法辨识的绝望,并非面对着永远循环的中国历史、鲁迅所表达的绝望的愤怒的回声。残雪的小说所书写的微观政治图景,酷烈、恐怖;但十分遗憾的是,那是人类历史的秘密之一,却并非中国社会与历史的“特权”。
从某种意义上说,残雪是当代中国文学中,唯一一个几乎无保留地被欧美世界所至诚接受的中国作家。笔者毫不怀疑有诸多中国作家比残雪拥有更高的国际知名度,但残雪或许是唯一一个似乎不必参照着中国、亦不必以阅读中国为目的而获得西方世界的接受与理解的中国作家。但具体的情形并非如此简单。
或许残雪的作品,确实作为一个“异数”告诉人们:并非所有的来自第三世界的作家们都在“以舍伍德·安德森的方式写作”。如果我们姑且搁置话语权力或后殖民讨论的理论观点,要阐释类似结论何以产生,一个相对贴近的答案是,人们——中国的、甚或西方的阅读者对“第三世界文学”、“中国文学”的、舍伍德·安德森式的预期视野与接受定式,先在地规定着人们对作品的解读与阐释。

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1876-1941),美国作家。1876年9月13日,安德森出生在中西部俄亥俄州克莱德镇的一个贫寒家庭。安德森认为物质至上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弊病。他认为物质至上正在毁掉美国:“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工业化时代。机械对人生活的影响无处不在。机器塑造了人们的风俗习惯,左右人们的见解。机器深入到我们的心中、思想和灵魂里,把我们本身变得自动化。”安德森尖锐地看到机械化对美国人生活的负面影响,抓住了那个时代美国历史的特点。这些都反映在他的作品主题当中。
面对一部“第三世界”的文学文本,人们索求着寓言,索求着关于民族寓言和社会命运的故事。而残雪的故事确实关乎中国的现实:关于贫穷,关于家庭中的权力与暴力,关于肮脏,关于身体的溃烂与环境的溃烂,关于窥视与流言,关于委琐卑微者对变动的希望与恐惧,关于梦中之梦,关于喋喋不休中的语言之墙——但这却是一处似乎可以指认却无从指认的深渊——由于笔者拒绝使用诸如“人性”类字样,因此姑且称之为灵魂的深渊。
然而,另一个有趣而相关的事实是,关于残雪,人们所可能提供的,是其作品所引发的“联想”:关于弗洛依德和创伤,关于迫害妄想和施虐、受虐,关于达利和超现实主义的,关于卡夫卡和变形与审判,关于贝克特和等待戈多,关于拉美文学和魔幻现实主义……似乎残雪本人一如她笔下的X女士是无从直接到达或触摸的,我们只有在无数熟悉的参照与坐标的不断衡定中,才能迂回地接近她那匪夷所思的世界。
毫无疑问,残雪并非外星异物或天外来客;她是中国文学对七八十年代之交20世纪的欧美文学破堤而入的最初反馈。但与其说是西方现代派文学造就了残雪,不如说是现代主义的写作方式应和了残雪的生命经验与文学想象;被现代主义文学所陡然拓宽的文学视野,对残雪说来,便是生命与想象的幽闭空间“剪开了一扇天窗”。

作家残雪
然而,尽管残雪异军突起的书写方式,使西方知识文化界更为轻松地接受了残雪,并可以在自己的文学脉络中不加迟疑地认可残雪小说的文学价值,但真正有趣的是,尽管他们是由于“文学”而接受了残雪,但他们的反馈方式表明,他们仍试图通过残雪而窥见并指认“中国”。
于是,在众多的西方、海外学者对残雪的介绍和评介之中,我们看到了两种潜在的对话或对抗:一是西方对于中国文学的接受定式,尝试将残雪阐释为社会寓言或政治寓言,从残雪的意象灵动、扭曲变形的梦魇世界中去指认中国“文革”时代甚或社会主义的历史;另一种则是拒绝这种潜在的优越与俯瞰,直截了当地认可残雪小说的世界意义,认可残雪的小说不必比照“中国”,便是大师级的作品,是世界文学视野中的新作,甚至是“新的世界文学的强有力的、先驱的作品”。

显而易见,“世界文学”,这个德国诗人、作家歌德在19世纪提出的文学乌托邦式的概念,在20世纪临近终结的今日看来,是一个已然遭到诸多质疑甚或批判的概念,因为这个美丽的梦想,无疑会掩盖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无所不在的不平等与权力关系;尽管类似权力关系直接呈现为全球的资源分配与经济利益,但却会同样鲜明尽管微妙地显影于文化领域,尤其是所谓“文化交流”之中。
因此,围绕着对残雪的定位与阐释,事实上出演着另一幕关乎“中国”的学术“小世界”中的微观政治,而且是有着一个怪圈式的结构方式:尽管有着西方学者所熟悉的语言与叙事形态,但他们仍会在这并非“舍伍德·安德森式”的作品中寻找所谓的“民族寓言”的理解,这间或是西方中心主义或冷战式思维的不自觉的显影;而强调残雪之为“文学天才”的意义,强调她贡献于世界文学的新的活力的价值,却以似乎停留在“前语言学转型”的审美判断与“世界文学”的乌托邦想象之中的方式,成就了一种对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霸权和冷战思维的反抗。
而在80年代的中国文化视野中,围绕着残雪的阐释,则显现了另一个重要的文化症候:从1985年,残雪登台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舞台起,她的支持者与辩护者便尝试以“自我”、“个人”、“个性”的书写来阐释残雪的世界。人们刻意地拒绝和避免讨论残雪小说的社会意义。这似乎是一个反例,质疑着中国社会对民族寓言与社会批判性的文本的需求与解读定式。
但是,人们间或忽略了在80年代,尤其是在1985年——新时期初年的阴晴不定的政治文化局面已成为昨日,于是,尽管政治迫害的记忆与忌惮仍影响着精英知识分子群体的文化建构过程,但思想解放运动的显著成果正预示着一个文学、文化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黄金时代的降临;于是,“自我”、“个人”、“个性”而非社会、政治,不仅是一个绕开政治迫害情结的策略,而且是一种文化反抗方式,其自身便是一个建构中的文化乌托邦与新的社会神话。
或许可以说,对于80年代新锐的文学批评家们说来,以“自我”或“个人”书写来指认残雪,出自一种特定时代的反抗与建构的文化需求,作为一种为作品、作家命名并为其合法性申辩的方式,也是在彼时所谓“庸俗社会学的批评方法”的重压下拓宽文化、批评空间的努力:通过非意识形态化,变政治化、社会学化的批评而为艺术批评。
但是有趣的是,这种文学批评——也是80年代特有的文化建构过程,不期然间成了某种突围表演。80年代后期,伴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残雪所归属的80年代精英知识分子群体开始意识到:当“个人”、“自我”不再是一个集体性的语词,不再是一种乌托邦或神话,那么它事实上将成为对“启蒙时代”、“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及使命”的解构性力量。或许可以说,这正是残雪作品原本潜在携带着的间或来自女性生命体验的文化僭越力量。
在笔者看来,这事实上已然显现了80年代中国的启蒙主义与文学现代主义话语之间的结构性的自相矛盾。如果说这便是“现代性话语的两重性”的话,那么,围绕着残雪和对残雪的阐释,事实上同样包含着80年代中国文学的世界想象与本土定位间的分裂与冲突,包含着知识分子自身角色及意义的分歧与自相矛盾:这一深刻的矛盾,在80年代终结处的社会动荡中一度被整合,不如说是被遮蔽,它将在90年代初重要的文化论争——人文精神讨论中再度浮现出来。

王晓明,1955年生于上海。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上海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主要参与者之一。
如果我们沿用线性历史观的表述,那么,残雪始终超前于我们的时代:不仅在1985年,而且在整个80年代的文化过程中。如果说她的书写方式曾再度为“人性”、“自我”、“艺术个性”等等“19世纪”的语词注入了生命,那么,残雪的书写本身,已然在解构这些概念及其文化根基:一幅涉及日常生活权力结构、微观政治的画面,一幅生存荒诞的变形梦魇,原难以支持“自我”或“人性”(即使是人性恶)的神话。尽管间或以X女士的方式讨论过“艰难的启蒙”,尽管事实上作为80年代精英文化的重要人物,但残雪在其90年代的作品中,以她的别一样的彻悟回应了“人文精神讨论”中的知识分子角色及其话语困境:
有这样一种守护,也可以说根本不是什么守护,只不过是坐在光秃秃的山下,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最后连自己也忘记了自己的所在。
…我将这称之为守护,为什么呢?
或者因为要找个借口,来填补内心的空虚,或者是一种辩解。
如果说文学的批评与文化研究或意识形态批评始终是中国的和关于中国文学研究所面临的另二个双重标准的困境,那么残雪无疑提供给我们一份双重意义上的丰盈。
(更多好文 请加小编微信happy_happy_maomi)









